一、烟花般的生活(上)
向左
再向右
对
就是那儿
茂密的黑夜丛林
闪着泪珠的微微光亮
就是你多年未见的萤火虫
--送给泡泡
2001年盛夏,你死了,然后我也死了。
当生命的萤火虫划过记忆的时空,让我们一同回到过去
一、 烟花般的生活
我喜欢研究星座,买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星座杂志。我还热衷于算命,天啊,我居然有两条感情线。我是摩羯座的,这个星座的人都有些诡异,喜欢做些毫无意义可言的事。比如说,我花很多时间用来发呆和布置我的小房间,我用不同款式不同颜色的格子布把墙壁包裹起来,在深绿色的床上放个长着雀斑的丑娃娃,我的书桌上还有一个玻璃鱼缸,里面有红色斑点的金鱼和粗糙的珊瑚,珊瑚发黑了,因为我常往鱼缸里滴墨水。我的朋友拉酷酷来过我的房间,他说我全神贯注地滴墨水的姿势很空灵,有一种大病初愈的感觉,像一幅蜡笔画,看着看着就身临其境了。他喜欢在这里看漫画或者朗诵伟大诗人普希金的伟大诗作或者昂首挺胸自言自语--像一个真正的文学青年一样。有天他在这里写毛笔字我在地上打滚,他和气地说我是心地善良的陶瓷娃娃,他说我是没有烦恼的,不会为青春哭泣不
会为生活困扰。
我没有听他说,我开始大声尖叫,于是他制止了我,他说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我
不能够这样。我没好气地走到阳台上伸懒腰,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阳台上有一盆装模作样的台湾竹,它像一个失恋的丑丑的女生在暗自伤神,风懒洋洋地吹过来,台湾竹开始琐屑地倾诉,我软软的头发竖起,拉酷酷说别动别动好像蒲公英,我惊喜地问真的吗真的吗?蒲公英是很漂亮很脆弱的植物啊,风吹啊吹,就会碎成满天星星。或者说,像是在宁静的城市黑夜,无所事事的烟花在空中争先恐后地爆炸。多美的图画啊!在这样的美景之中我不禁发出"我是谁"的疑问。那么,我是谁呢?
"啪"的一声响。
平淡的日子像弥漫开来的璀璨烟花,朵朵都是我眉眼之间的忧愁。
你们好,我叫小康,17岁,在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念书。我有一群与我一样特别的"狐朋狗友"(他们有的会用扑克牌算命,有的会在雨天背诗,有的敢于穿纸做的衣服上街,还有的会在咖啡馆点一份甜点从一点坐到一点半,从一点半坐到两点,从两点坐到两点半)。我们每次聚在一起就会集体抱怨生活的平淡无聊,抱怨天气不好,也抱怨刺激的事情不能每天发生。抱怨归抱怨,还是开心的事多一点,我们有水果有巧克力有越来越多的真理。我们相亲相爱,温柔以待。拉酷酷说朋友是我的太阳,是透过啤酒瓶底看到的蔚蓝大海,是黑房子里蓬勃向上的凤仙花,我和朋友们永不分离,拉酷酷说的话我很相信。拉酷酷说这话谁都会讲,只要你闭上眼睛想想。这样的大学生活,任何人都有可能突然发出感叹,而这样的感叹很有可能会升华成真理。时刻拥有真理的生活真可爱!
我于是闭着眼睛想:清早起床要喝东宝,锻炼身体真真好;然后我像头异兽行色匆匆,以寻找猎物为目的,穿过一条沥青街道,和一排兔子笼似的小卖部,突然有一幢像水井般深邃像湖水般透明的建筑出现。天啊,我又来了这里。OK,我现在稳当地站在一家叫作"木头吧"的咖啡馆门口并若无其事地环顾四周:"木头吧"的老板想必也是个有品味的人,大门是用粗糙的原木钉成,顶上还有个红色的荷兰式木风车,风一吹就转起来,我便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六,数到二十的时候它停了。有意思的是还有一扇绿色的玻璃窗,用荧光粉涂抹出歪歪斜斜的汉字,比如说:祖母快跑,这里的火山爆发啦。
在诡异又暖昧的玻璃上,我能看见自己的样子:整齐的西瓜头,白色T恤,灰色口袋裤,黑白相间的帆布鞋,还背着酷狗牌的红色书包。这种色彩搭配很奇怪,其实我天生对色彩敏感,敏感到会做出生理上的反应,绿色使我安静灰色使我哀伤棕色使我焦虑黑色使我糊涂白色使我像喝了大杯自来水一样透心凉又透心凉。我常常因为自己绝妙的色彩搭配而暗自惊喜,小时候因为有天我无意地画了红色的天空和黑色的云彩,爸爸妈妈就请了一个刚刚师范毕业的"流氓"
教我画画。那个人油头粉面,有狐臭,喜欢骂人和挖鼻屎,他常常骂我是猪,有时候还会揣我的肚子,还有次因为和女朋友吵架而打破了我的头,然后逼我跟妈妈讲是自己摔的。这严重地滋生了我的自卑情绪,从此开始了我怀疑自己怀疑一切的悲惨生活,怀疑的程度到了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手指的个数,不敢相信吞进肚子的食物。一直到现在,当我在喧闹的食堂打饭的时候,在寂寞的水房洗衣服的时候,当我在花园偷花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他阴森森的眼睛在死死地盯着我,令我逃不开躲不了。直到小学三年级,爸爸妈妈发现我除了画了一幅叫作《会跳舞的鸡》的蜡笔画以外在美术上没有丝毫进步,这才打消了他们想培养一个艺术家的念头,于是辞退了老师,从那以后我才敢于面对自己与周边
的环境,我终于从美术老师的阴影中看到了光明。
我之所以会从爱好美术改成爱好写作,首先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项很高尚的活动,我刚刚有当作家的打算时就爱上了写作,我觉得它是我的精神振奋剂(千禧年能出一本小说是我的短期目标,成为具有超现实风格的新锐画家、先锋小说家、另类诗人是我的长期目标,也是我写作的初衷和持续写作热情的根本原因)。还因为我曾经在杂志上看到的一个故事:在一栋学生公寓里,一个女生凌晨三点起来上厕所,当时窗外风雨大作,在厕所门口看见一名戴黑色墨镜穿长风衣的男人在拖地,她想这么晚怎么会有人在拖地,想啊想还是回寝室睡觉了。但是第二天,公寓里人心惶惶,大家告诉她前一天晚上出了命案,一个女生被杀了,她推算了一下发现与她上厕所的时间相吻合,她仔细想,啊,原来那个拖把其实就是被杀的女生的尸体!我看完后不敢晚上起来上厕所,甚至不敢看拖把,还连续做了几天噩梦,我因此相信文字具有无可替代的视觉冲击力,它能让人生病甚至着魔,把它当作一个爱好实在是体面又风光。
拉酷酷也是中文系的,他说他要出一本诗集,封面一定会全是河马的大腿与梅花鹿的眼睛,而且他说他以后肯定会出名,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为了早一点,他搬出寝室,和外语系的丁丁和设计系的西西坨一起在学校附近租了三室一厅的套间,他在他的房间里装了电脑和音响,铺了印有大小不同的圆圈图案,在墙上贴恩雅的海报。拉酷酷对我说你可以常来,于是我常常留宿这里(后来干脆搬过来了),与他讨论关于文学的严肃话题,当然这只能成为我们逃课的理由,因为当我们发现谈话实在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兴高采烈地约上一对同居密友丁丁和西西坨下楼买消夜,然后坐在客厅的地上,说无聊笑话或鬼故事,每当说到无话可说时,我们便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讨论,针对很长一段时间的虚度做一个检讨,当然,很快又成为不必惭愧的理由。
其实我们四个的性格是不同的,我的话很少,拉酷酷的话比较多,而且边说边手舞足蹈,丁丁处于中间,为了炫耀他学的专业是英文,所以说话喜欢夹带英语,西西坨的话很少但是动作很多,因为她在减肥,所以她常常会旁若无人地跳健美操,就算音响开到最大,我们在热火朝天地打扫卫生,她还是会旁若无人地跳。我们每天的安排也不一样,我会去教室,因为每次同学都会带好多杂志去,这样可以省去泡图书馆的时间;下课后我常常会去我朋友开的小书店帮忙,那里离拉酷酷的住所不远。
拉酷酷不会去上课,天打雷劈也要待在他的房间里睡觉听歌玩一种叫做"大富翁"的电脑游戏,实在是饿了就打电话叫外卖。丁丁和我们其实并不熟,因为他老是消失,突然打电话来说在上海或长春,他还有个至今没有明确身份的韩国女朋友,有时候深更半夜带她回来,还没看得清就把门给拴了。西西坨把很多时间花在上网吃冰激凌买衣服上了,陪她逛街是若干痛苦的事情当中的一种,她对衣服和化妆品的挑剔已经到了我和拉酷酷无法忍受的程度。她喜欢穿粉红色小吊带白色小棉袜棕色小皮鞋,然后梳好头发去见网友,她把这称为打猎,因为每个网友都心甘情愿地陪她闲逛,他们都说愿意为她付出一切(比如说大袋的果冻,精装的时尚杂志,新出的磁带等等),不过我的呼机常常收到她发的消息:"有个猪头好丑,马上打我手机叫我回去,救我!"西西坨惯用的脱身伎俩是委婉地对网友说: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西西坨说自己与世无争,见网友不是争,而是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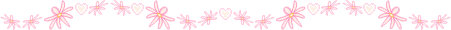
一、烟花般的生活(下)
我们常常在一起举行一些有意思的活动,听拉酷酷念诗,听丁丁讲爱情的起源,看西西 坨跳舞,买很多零零碎碎的小食品做拼盘,还讨论各种现象和各色人等。这样的生活看起来五光十色,实际上无聊得要命,但是我们又找不到比这更积极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只好凑合着过,并且面带享受的表情,我们把这样的生活叫做"模拟白领生活",虽然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幸福的爱情,但是每个人都不可一世,都喜欢叹气,都喜欢辱骂世事无常,但无论如何,我们过得还是很快乐的。
我常去帮忙的书店叫作"纸片",离拉酷酷的房间没多远,这里专卖一些不起眼的书,哲学或美学的,甚至还卖诗集。书店有灰底白字的招牌,和大捧大捧的黄玫瑰,反映出老板大方而不招摇的性格。老板七月是我朋友,在经济系读书,她常常来拉酷酷这里找我,给我们带零食和饮料,于是她和拉酷酷很谈得来。但是他们认识的交集只有我,所以所谓谈得来也只是谈论我谈得来,拉酷酷说既然他那么喜欢谈,我就和她认真谈吧,不然断我的粮那可不好。七月是一个与我之间存在着高于友情低于爱情这种自欺欺人朋友关系的女孩,这种关系让我不甘心却又着迷。她有一头染成板栗色的头发,美丽而憔悴的脸。她很容易被人爱,她说她很享受被人爱的乐趣,可以任意差使她的追求者,可以在各种场合撒娇或者发小姐脾气,那滋味,简直只有公主才能拥有!
我认识七月时她的父母还没有去美国,我们在同一所高中,她高我两届,是文科班的红人,属于开学生大会时和校长坐一排的那种。我和她的相识缘于一次和她一起听文学社讲座,她主动找我讲小话,并问我喜欢喝哪种牌子的牛奶喜欢哪种牌子的冰激凌,还问了我喜欢哪种类型的女孩,后来她频频来找我,毫不疲倦地说着她父亲的繁忙母亲的倔强男朋友的似水柔情奶奶的孤苦伶丁,以及对未来的设想对生活的构造甚至为出国还是考大学感到身心疲惫无法定夺。我当然会很乖地听,甚至还觉得她说得十分精彩,但也许根本没听,只是没有插嘴罢了。她是我文学创作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所具有的人格魅力能自然而然地凸现在纸上。亲爱的七月头一扭就把将登上去加州的飞机的父母扔在脑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机场。亲爱的七月和我上了同一所大学,她常常告戒我不要被漂亮女人欺骗感情,她说漂亮女人都是有毒的。亲爱的七月说男朋友不闲多还不随便挑,但是每次到了最后还是一个人吐着烟圈在酒吧喝得一蹋糊涂并发誓再不要为男人流泪。
而我和她一直像糖果和糖果纸一样不可分开,因为我是她发泄倾诉欲的对象,而且我们之间存在一种可无限扩大的张力,她做事有根有据有魄力并且善于推理,而我冷了不知道加衣热了不知道脱衣总是需要别人的照顾。这种张力加上恍惚的距离使我与她的交往一直保持最佳的情绪状态,奇妙的***像刚刚出炉的葡萄牙蛋塔一样甜美。就像那天晚上在"木头吧",美丽的七月望着我像大方的顾客捧着一件爱不释手的非卖品,我不能采取任何措施,即使她套着那件ESPRIT的短衫,像睡衣似的可以露出暗暗的乳沟,我也只能一如既往定定地看着调酒师,托着腮任凭自己怎样的心猿意马,顶多斜斜瞥她一眼,瞥见她闪烁如烟花的电眼像在审视整个社会,然后用涂着暗红色指甲油的手优雅地托起一杯雷司令轻轻啜一口,整个过程让我心里一阵阵风吹草动。七月是一个金黄色的理想,我绕着这个理想大声唱赞歌。
在长沙这个时刻爆发着理想闪烁着***活跃着矛盾的新都市,空气中总是阴霾阵阵的,持续久了,就染上一种细小的霉点。整个城市的浮躁和人们无所适从的叹气声叽哩呱啦地游荡在上空像遮阳伞一样。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快速运转,像一台大型机器中密密麻麻的齿轮,一个带动一个丝毫不敢松懈。在这群老鼠般匆忙鳄鱼般冷漠的人群中,是有一个人在漠视这些乱七八糟的路边摊、穷奢极欲的广告牌、怪里怪气的滑板少年,然后走来走去,孤独地哼歌,停下来思考。那是我嘛,身体瘦弱,思想浅薄,愿望多得可以连成一条河流。我其实是一个有着平淡人生观的人,喝各种不同牌子的果汁,喜欢看周星驰的喜剧片,有时候骑自行车会摔跤,还幻想写一本小说却并未付诸行动仍停留在宏伟的构思当中,而我的朋友们却对我"伟大的创作"信心十足,他们觉得从我眼神中那种欲罢不能的进取心看出总有一天中国小说界的权威人物非我莫属,尤其是拉酷酷,他说我天生具有文学家的气质,我天真而且无辜,但在大脑里转圈的全是有见地的思想。
当然,我知道写作并不是一种很轻松的活动,尽管我以前无比景仰康德的游戏说,可是写作确实不是游戏,也不是过剩营养物的发泄,它需要的是自虐般的思考。我喜欢思考可是一旦陷入思考我便会回忆,而回忆是一种倒退的思考,我始终不愿正视回忆而只会强调现在,所以写作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与紧张。是的我知道,对于我这样一个自负、平庸、神经质的男生,写作是最现实的工作,而出一本小说无疑对虚荣心是一种极大的满足,也能为天是蓝的树是绿的土是死黄色的平凡生活增色不少,甚至于可以为我这小半生不期而遇的感情问题生活问题学习问题作一次完美极端又客观的总结报告。更重要的是,在七月的书店里,她常常会把我这样介绍给她的各种朋友以及一个经常光顾的客人:他叫康,学文学的,很有思想,现在在写小说,他肯定会红的,我们这里以后会专门卖他的书。你看看,我非当作家不可了。
我不知道七月背着我是怎么描述我的,反正她的朋友都对我很感兴趣,因此"纸片"的生意就很好。尤其是有个叫五月的女生,是念工科的,她的头发很长很干燥,她的脸又长又瘦,面无表情,很胆小怕事的样子。她迷恋文学,下课后就会停留在"纸片"不走,站在一个角落用一种类似于惊恐的眼神打量我的全身,她也买了很多书,她很关注一些不怎么出名的小作家。后来,七月告诉我说她疯了。七月说,五月认为自己变成了蝴蝶,她把蓝色的油漆图在脸上,从早到晚地歌颂星星和月亮,还连续两次在家门口走失。七月说真可怜,好好的女孩子变成这样,七月说在医院看她的时候她正在抽烟,她对七月说等着吧天鹅们要来了,七月放下花就走了,听见身后的病房里传来她骇人的惨叫。以后再也没有见五月来过"纸片",我甚至有点想念她来。也许这不叫想念,这只是我沉默时的一些状态,也是我对可怜的五月的好奇。
"怎么会这样,七月你告诉我,人怎么会疯呢?"
"就是这样。"
"就是怎样?"
"想多了,就这样了。"
"怎么就想多了。"
"像你这样。"
"那我也会疯吗?"
"指不定。"
"那我疯了怎么办。"
"就去医院看你。"
"我不会疯的。"
"那就不去医院看你咯,这还不简单。"
"我要坚持写小说。"
"写吧。"
我极其认真地写下"再见萤火虫"五个字作为小说的名字,小心翼翼地继续往下写:
"我在做一个梦:那是一座新世纪的美丽废墟,具有钢筋混凝土砌成的外形和五彩霓虹般柔软的内脏,无数辆起重机和压路车在孜孜不倦地作业,电线大把大把缠在一起吱吱吱迸发蓝色的电光,我在黑暗的人群之中穿梭,提心吊胆地找一个方位,是的,并非有人在追踪我,而是我预知了这座城市即将沦陷的危机。时时有建筑物垮掉和爆炸的声音在耳边继继续续地响着,眼前断断续续闪现出电视屏幕的雪花、一棵将倒的古柏、堆得有三层楼高的啤酒瓶这些奇怪的画面,然后,我定住了,我看见天桥上有个白色的影子纵身跳了下来。是一个女孩的身影。"我转动着那支有透明笔帽的日本水笔,等着看泡泡读完后是迷惑不解还是惊讶万分,我很在意朋友对我小说的看法,小说像我的心脏,新鲜地呈现在朋友面前,仿佛稍有让我不适的评价就会供氧不足。如果说我的好朋友胡同是个百分之百的男孩,那么泡泡就是个百分之百的女孩。
胡同一向对写作抱有愈演愈烈的仇视态度,仿佛我写出的只字片语都会给他一阵无法预防的流感,这正足以说明文字的力量是伟大的。他讨厌文学青年说话时的拐弯抹角,绝对不赞成我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在他看来这都是不正常的。而泡泡此时总能和我惺惺相惜,总能充当最负责的读者和评论家。她是个崇拜浪漫诗歌对左拉的自然主义怀有敌意的美丽少女,有披肩的头发和整洁的打扮配上用手将头发往耳后一挂的熟练动作,像扇贝般纯洁像琵琶虾般晶莹,一个人的时候她会写象形文字和诸如"北方有孤独的内陆河,内陆河有自己的美学"的抽象诗句,也会投入地看言情小说并在适当的时间微笑或者叹息或者哭泣,讲话时细声细气措词委婉为他人考虑,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她近乎于苛刻,她向往柏拉图式的纯粹爱情,需要和风细雨的呵护和轻描淡写的安稳,于是拒绝了那些肤浅男孩提供的无数甜美的应酬,至今仍与我和胡同保持着亲密无间的死党关系。
我不得不介绍一下现在的状况:
现在已经九点,我、泡泡还有胡同正坐在装修得像酒店一样豪华像法院一样空旷的理学院大楼的小玻璃屋里(胡同说这里使人产生想点菜的欲望),这个抢手的地盘本来是供数学系的学生自习用的,可我们在六点钟就抢先占领了。我们的目的是自习,可结果都成了度假,因为我们除了带书还带了碳酸饮料和盒装水果,我们现在的亲密无间归功于上个学期相识后一整个学期的感情培养,付出的代价则是临期末考前几个星期的通宵达旦才换来了勉强及格,没有一科需要补考或重修,这个学期我们重拾信心准备将新世纪大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发扬光大,可每次自习都是为别的活动掩人耳目自抬身价的,我进行我"伟大的创作",泡泡会带一本咖啡色调的《纪伯论文集》或专心致志的削指甲,而胡同则呼呼大睡,若醒了就开一两句诸如"印度警方花了两个月时间确定那名头部被利器敲击三十多下的男子属于他杀"之类的弱智笑话或者用walkman听疯狂英语。我们这种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大学生活令这间漂亮精致的玻璃教室多少有些暴殄天物。
"亲爱的,你的语言很个人化,是我喜欢的语言,只是读起来比较干涩,看不出有多少丰润的真情实感,你可以更煽情一点比如说安排女主角最后死掉,这可以达到梦境与现实的统一,当然只是个设想。"泡泡坐在桌子对面,穿着淡绿色娃娃领衬衣和白色牛仔裤,两只手比划着像两只正在交配的小蝴蝶飞来飞去,头上是明亮的日光灯,她的存在很唐突,给我造成明显的视觉冲击,就像是突然从日光灯里掉下来的,令我每次抬头看见她就会惊讶一次。"可以考虑吧,我可不希望我的小说中出现一些拙劣的校园情节变成千篇一律的校方纪实报道,这种工作有很多人在进行,我要做的是表现埋伏在大学校园中那些特别的少年酷酷的爱情观和对未来的思考。他们是那么的无所畏惧,那么的雄心勃勃,而他们的心灵却又那么的弱不禁风,生活在梦想的天堂中,整日唱歌跳舞,只喝矿泉水吃精致好看但不太可口的食物,爱着身边每一个人,对所爱的人毫无保留,他们是一群真正的新新人类。"
"是类人猩猩吧。"胡同睡醒了并伸了一个完整的懒腰。
我们笑成一团,肆无忌惮地打情骂俏。凶巴巴的数学系导师推开了小巧的玻璃门,我见他梳着偏分头,有些秃,穿中山装,拿个人造革的公文包,像个七十年代农村计生委的干部。原来他是来赶人的,他容不下这么严肃安排的大楼里出现几个自由、放肆、慵懒的新青年像开派对一样疯狂的事实。神经兮兮的闷热夜晚,日子像一块巨大的柠檬派。我的朋友你可曾感到,这些平淡香酥的日子,用手轻轻挤压它们便会流出一股热气腾腾的粘稠的深红色汁液,甜蜜得令人委屈,仿佛预示一种带有轻微野性的故事在天天如此的生活中衍生,然后流淌成一种悲剧的形状。而这个故事的神秘情节像船锚一样一刹那就勾住了你的心,惊讶地回头一看。拉酷酷曾说:娃娃看天下,世界无限大。


